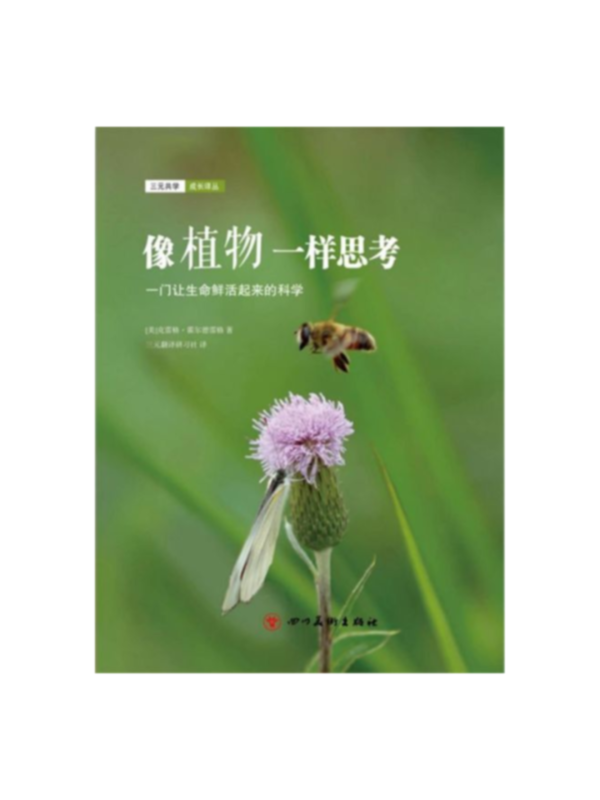商品詳情
一株植物從人行道上的裂縫中生長出來,植根於一個關係的世界中。
它的根朝著地球的中心向下生長。它們一邊勘探和改造土壤,一邊飲用水和一系列礦物質。嫩枝和葉子朝相反方向生長——向上生長到空氣和光線中。樹葉向這些元素敞開大門,接納它們。植物將土壤中的水和礦物質與空氣和光一起帶來,並以其謙遜的方式創造出奇跡——它創造出自己的鮮活物質成分。植物生活在這種環境中,它會根據自身的內部模式生長和轉化,並且會隨時調整自己以適應環境的變化。
這意味著在裂縫中長大的小而緊湊的蒲公英可能與在花壇中僅幾英尺遠的地方作為“雜草”熱情地生長的蒲公英截然不同。儘管,作為一種地方性生物,植物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可移動的,但它是動態的、有聯繫的、有彈性的,並且在它不斷變化的生命中,總是與它生長的世界相關。
為什麼我們不能像植物那樣?顯然,我們不能寄希望於我們的身體能夠漫步到院子裡去,在大地上生根,然後利用太陽的光線吸收空氣,水和少量的礦物質。但是我們可以寄希望於自己擁有植物那樣的思考能力。如果我們人類能夠以植物的生長方式去思考,世界會是什麼樣子?想像一下,我們的思維變得如此靈活,不再僵化、靜止,不再像物體一樣,而是不斷成長、轉化,必要時也會消亡。就像植物形態一樣,如果我們的行為產生於我們與環境之間的敏感關係,會怎麼樣呢?這難道不是一場值得努力的革命嗎?
在這本書中,我想表明,如果我們有興趣以更深的方式解決我們今
天與地球的不可持續關係,我們對世界的思考方式需要徹底地重新定位。據我所知,沒有比植物更好的人類可持續化的思考模式。問題是,我們的頭腦已經愛上客體和事物。我們已經完善我所說的客體思考。客體思考理所當然地認為自然是由物理事物和實體組成的,它們在客觀物理規律的基礎上相互作用。
這是一種觀點,讓聰明的智性頭腦能夠將自然理解為一個複雜的機制或系統,並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和擺佈自然。但是,在成為一種機制或系統時,自然也變成了一種抽象化。在我們看來,我們正在面對的是“外面的事情”,一個我們實際上不參與的外部性世界。
除非我們是高級科學家,否則我們與原子、分子、基因、激素或神經遞質沒有密切關係,但我們有理由認為這些我們沒有切身體驗的或與我們無關的“事物”是我們世界的基礎!因此,今天誰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認為自己已經融入了這個世界的鮮活結構之中?我相信,也將會爭辯,客體思考是我們與世界不可持續關係的基礎,因為它使我們與自己試圖以健康、可持續的方式理解和互動的世界格格不入。又因為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和無處不在,所以客體思考是一種世界觀,自然的剝削者和環境活動家都可以分享。
從客體思考的角度來看,可持續性是通過現有的人類能力實現的一個綱領性目標,而教育則是培訓人們(以傳統方式)解決緊迫的環境問題的一種手段。雖然這種努力在短期、長期和根本上特別重要,但它們終將會失敗。
我認為,長期的可持續性不會通過技術修復或環境法來實現,儘管這些可能很重要。它需要一種不斷進化的心智狀態——更確切地說,是一種不斷進化的心智變動——在這種狀態中,我們體驗到自己作為行星進程的有意識的參與者,並逐漸能夠在生命本身的動態和相互聯繫的本質之後,塑造我們的思考和行為方式。這是一個很高的要求,因為它意味著超越客體思考,這種思考的好的和不好的方面在人類頭腦中已經佔據了太長時間的。但是和所有大型任務一樣,你會尋找到一個重新開始工作的地方。